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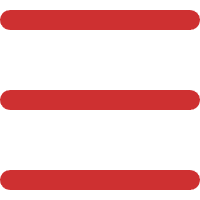
王守觉出生在1925年的上海,那是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稍大些,他又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阴影下。

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王守觉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思虑,“为什么”与“怎么改变它”牢牢占据了他的脑海——为什么我国科技落后?为什么书里都是洋人的名字、洋人的学问?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堆问号让王守觉慢慢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而他坎坷的求学经历,更让他建立起对独立思考、在实践中获得知识的信心。
自学成才的“名门之后”
王守觉出身于苏州书香名门,家境优渥,家中人才辈出,只他这一辈便人才济济。谁料王守觉作为家里最受宠的“老幺”,只在小学阶段有持续系统的学习,之后竟差点无学可上。
1936年,11岁的王守觉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一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王守觉学业被迫中断。1937年11月,他随年迈的双亲逃难,一路颠沛流离,直到1938年方在昆明落脚。1939年初,王守觉进入昆明天南中学读初三下学期。
眼见初中毕业,他却因病住进了医院,只能辍学。身体好转一些后,14岁的王守觉不甘心在家赋闲,就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他养过猪、修过钟表,还自制门锁拿到市场上卖。
1942年初的一天,他在昆明街头撞见了一个初中同学。同学行色匆匆,告诉他“还有半年就要考大学了,得抓紧时间”。王守觉内心一阵悸动:“他们都读大学了,我怎么办?”
他要考大学。但因为初中之后上学不多,家里人都不大看好他,既不鼓励也不阻拦。青春期少年的自尊心正强,王守觉便独自关起门来看书,遇到问题也不愿马上去问家人。他的办法是先做题,实在不会就参照答案,答案看不懂再去翻书、思考。用这个方法,他很快搞懂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但英语有点犯难,他就把家里的英文杂志都搜罗出来,遇到生词就对着词典弄清词义、搞懂全文,然后把文章背个滚瓜烂熟。
他就这样准备了半年。1942年夏天,王守觉想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但因没有高中生证明,只能报考大专。虽然考上了西南联大的电信专科,但他心有不甘。后来,他如愿考入同济大学电机系。
上大学后,王守觉的自学能力更有了用武之地。同济大学有一位从德国留学回国、讲授电工理论的教授,他喜欢国外的教育模式,讲课少、考题难。一次考试,由于题目出得太难,全班19人只有3人及格,独王守觉考了96分,让这位教授震惊不已。
从“东亚病夫”到活力四射
1940年秋,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在昆明站稳脚跟才一年多的同济大学不得不第六次迁徙,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李庄,师生生活极为艰苦,学生们衣衫破烂,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简陋的宿舍里,伙食差而量少,常常食不果腹。
本就体弱多病的王守觉,难以坚持正常的学习:1/3的时间是自己走到课堂,1/3的时间要在同学的搀扶下去上课,另外1/3的时间躺在床上。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东亚病夫”,笑他弱不禁风。
他不服。大二那年,王守觉就地取材,从河滩上找来两块石头凿成圆饼,中间穿上一根竹子,一个石担就制成了。他打算用石担练习举重。毕竟身体虚弱,再加上不太懂举重动作要领,王守觉第一次练习时,一个重心不稳,竟踉跄着摔了个跟头。他不气馁,每天坚持跑步并练习举石担。不到两年,他就可以单手举起30多斤的石担,后来双手可以举起140斤。他的体质逐渐好起来,成了一个健壮、活力四射的年轻人。
王守觉一直希望中国科学能从“东亚病夫”状态走向健壮、活力四射。
在学术生涯的前30多年,王守觉将自己善于学习、肯于钻研、勤于实践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他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并亲自下厂制备用于批量生产的设备,保障了其在我国第二代电子计算机中的应用;他利用硅平面工艺制成我国第一只硅平面工艺晶体管,为我国研制应用于“两弹一星”的微型计算机铺平了道路;他用自制的图形发生器自动制版技术制成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版,解决了制约集成电路发展的关键问题,这项工作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他还提出一种新的高速集成逻辑电路“多元逻辑电路”,大幅提高了电路运算速度,比日本最早发表的集成模糊逻辑电路论文还早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半导体所),王守觉和他的哥哥王守武等带领团队制成中国第一个(批)硅平面型晶体管和中国第一块(批)集成电路,支撑服务了“两弹一星”功勋计算机“109丙机”的研制。
回顾从大学毕业到年届六旬、卸任半导体所所长之间的36年工作,王守觉总结说:“这一阶段我主要是按照国家建设计划的要求,跟踪国外半导体电子技术,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这些只是王守觉人生精彩篇章的上篇。此后30年里,他从人工神经网络的硬件化实现(神经计算机)、模型与算法研究到仿生模式识别,再到高维仿生信息学、三角形坐标系与计算机图形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偏离国外的通用方向愈来愈远。
这些被王守觉称作“第二阶段”的工作,是他一生心系祖国科学事业、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亲身实践。
甘做“花匠”,耕耘第二春
1995年,王守觉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神经计算机,并开展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今天看来,王先生是国内最早一批真正做人工智能研究的人。”王守觉的学生、半导体所研究员李卫军说。
李卫军1998年在半导体所硕博连读,他回忆说:“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懂人工神经网络。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从事人工神经网络研究’。人家就问:‘什么神经网络?是不是研究神经病的?’”
“有了神经计算机后,王先生就想着拿它做点什么。”李卫军说,开始是用它研究图像处理,做人脸识别、手指静脉识别等图像和视频分析方面的工作,后来逐渐做到了仿生模式识别领域;在仿生模式识别基础上,发现很多信息其实可以对应高维空间上的一个点或者一些分布,于是又发展出高维空间点分布分析与模式识别、高维仿生信息学等一系列工作。“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沿着这些方向发展新的方法。”李卫军说。
王守觉投身“第二阶段”工作30年,相继提出仿生模式识别和更为广义的高维仿生信息学新基础理论,并在企业与地方的支持下发展了超低数据量(48字节)人脸识别技术及浮动网格的人脸与表情自动生成等实用技术。
在科研工作上,他一心求“新”。关于此,王守觉有一套“花匠论”。
“从邻居园子里摘一些花插在花瓶里,既美化环境,也能使我们认识更多花种,这是很有必要的;但它不能代替翻耕自己的土地并播下自己的花种。”王守觉说,“我们要从邻居那里取得经验,根据自己土地的情况耕作,长出自己的花,哪怕相对较小和较少一些……我们不做美丽鲜花的观赏家和评论家,愿做平凡而艰苦劳动的花匠,在生产实践中去找我的耕作园地。”
1984年,王守觉被派往美国几所大学作学术交流报告,落实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杰出学者互访计划。几次会后,不断有中国人问他:“你在美国待了多少年?在哪所学校念的书?”
这让他哭笑不得。他感慨:“百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现实,使中国民间和社会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洋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这就对中国超越‘洋拐棍’的工作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我第二阶段这30年来的工作说明了中国人是聪明能干的,任何新领域只要按照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明的规律性,破除对洋人权威的迷信,刻苦拼搏,就能在5年左右时间走到学科的最前沿,接近或超过国际上的最高水平。”
王守觉曾对参与撰写他科研活动传记的作者团队说:“我的科研活动传记第一阶段工作很好写、很明确,但第二阶段工作很难写,因为不少工作都是‘开着口’的,有待进一步系统化与完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希望我第二阶段的科研工作能够成为年轻人超越世界最高峰的一段梯子,在科学方面实现中国梦,也实现我的梦。”
(《中国科学报》)
王守觉出生在1925年的上海,那是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稍大些,他又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阴影下。

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王守觉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思虑,“为什么”与“怎么改变它”牢牢占据了他的脑海——为什么我国科技落后?为什么书里都是洋人的名字、洋人的学问?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到哪里去了?
这一堆问号让王守觉慢慢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而他坎坷的求学经历,更让他建立起对独立思考、在实践中获得知识的信心。
自学成才的“名门之后”
王守觉出身于苏州书香名门,家境优渥,家中人才辈出,只他这一辈便人才济济。谁料王守觉作为家里最受宠的“老幺”,只在小学阶段有持续系统的学习,之后竟差点无学可上。
1936年,11岁的王守觉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一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王守觉学业被迫中断。1937年11月,他随年迈的双亲逃难,一路颠沛流离,直到1938年方在昆明落脚。1939年初,王守觉进入昆明天南中学读初三下学期。
眼见初中毕业,他却因病住进了医院,只能辍学。身体好转一些后,14岁的王守觉不甘心在家赋闲,就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他养过猪、修过钟表,还自制门锁拿到市场上卖。
1942年初的一天,他在昆明街头撞见了一个初中同学。同学行色匆匆,告诉他“还有半年就要考大学了,得抓紧时间”。王守觉内心一阵悸动:“他们都读大学了,我怎么办?”
他要考大学。但因为初中之后上学不多,家里人都不大看好他,既不鼓励也不阻拦。青春期少年的自尊心正强,王守觉便独自关起门来看书,遇到问题也不愿马上去问家人。他的办法是先做题,实在不会就参照答案,答案看不懂再去翻书、思考。用这个方法,他很快搞懂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但英语有点犯难,他就把家里的英文杂志都搜罗出来,遇到生词就对着词典弄清词义、搞懂全文,然后把文章背个滚瓜烂熟。
他就这样准备了半年。1942年夏天,王守觉想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但因没有高中生证明,只能报考大专。虽然考上了西南联大的电信专科,但他心有不甘。后来,他如愿考入同济大学电机系。
上大学后,王守觉的自学能力更有了用武之地。同济大学有一位从德国留学回国、讲授电工理论的教授,他喜欢国外的教育模式,讲课少、考题难。一次考试,由于题目出得太难,全班19人只有3人及格,独王守觉考了96分,让这位教授震惊不已。
从“东亚病夫”到活力四射
1940年秋,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在昆明站稳脚跟才一年多的同济大学不得不第六次迁徙,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李庄,师生生活极为艰苦,学生们衣衫破烂,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简陋的宿舍里,伙食差而量少,常常食不果腹。
本就体弱多病的王守觉,难以坚持正常的学习:1/3的时间是自己走到课堂,1/3的时间要在同学的搀扶下去上课,另外1/3的时间躺在床上。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东亚病夫”,笑他弱不禁风。
他不服。大二那年,王守觉就地取材,从河滩上找来两块石头凿成圆饼,中间穿上一根竹子,一个石担就制成了。他打算用石担练习举重。毕竟身体虚弱,再加上不太懂举重动作要领,王守觉第一次练习时,一个重心不稳,竟踉跄着摔了个跟头。他不气馁,每天坚持跑步并练习举石担。不到两年,他就可以单手举起30多斤的石担,后来双手可以举起140斤。他的体质逐渐好起来,成了一个健壮、活力四射的年轻人。
王守觉一直希望中国科学能从“东亚病夫”状态走向健壮、活力四射。
在学术生涯的前30多年,王守觉将自己善于学习、肯于钻研、勤于实践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他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并亲自下厂制备用于批量生产的设备,保障了其在我国第二代电子计算机中的应用;他利用硅平面工艺制成我国第一只硅平面工艺晶体管,为我国研制应用于“两弹一星”的微型计算机铺平了道路;他用自制的图形发生器自动制版技术制成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版,解决了制约集成电路发展的关键问题,这项工作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他还提出一种新的高速集成逻辑电路“多元逻辑电路”,大幅提高了电路运算速度,比日本最早发表的集成模糊逻辑电路论文还早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半导体所),王守觉和他的哥哥王守武等带领团队制成中国第一个(批)硅平面型晶体管和中国第一块(批)集成电路,支撑服务了“两弹一星”功勋计算机“109丙机”的研制。
回顾从大学毕业到年届六旬、卸任半导体所所长之间的36年工作,王守觉总结说:“这一阶段我主要是按照国家建设计划的要求,跟踪国外半导体电子技术,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这些只是王守觉人生精彩篇章的上篇。此后30年里,他从人工神经网络的硬件化实现(神经计算机)、模型与算法研究到仿生模式识别,再到高维仿生信息学、三角形坐标系与计算机图形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偏离国外的通用方向愈来愈远。
这些被王守觉称作“第二阶段”的工作,是他一生心系祖国科学事业、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亲身实践。
甘做“花匠”,耕耘第二春
1995年,王守觉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神经计算机,并开展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今天看来,王先生是国内最早一批真正做人工智能研究的人。”王守觉的学生、半导体所研究员李卫军说。
李卫军1998年在半导体所硕博连读,他回忆说:“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懂人工神经网络。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从事人工神经网络研究’。人家就问:‘什么神经网络?是不是研究神经病的?’”
“有了神经计算机后,王先生就想着拿它做点什么。”李卫军说,开始是用它研究图像处理,做人脸识别、手指静脉识别等图像和视频分析方面的工作,后来逐渐做到了仿生模式识别领域;在仿生模式识别基础上,发现很多信息其实可以对应高维空间上的一个点或者一些分布,于是又发展出高维空间点分布分析与模式识别、高维仿生信息学等一系列工作。“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沿着这些方向发展新的方法。”李卫军说。
王守觉投身“第二阶段”工作30年,相继提出仿生模式识别和更为广义的高维仿生信息学新基础理论,并在企业与地方的支持下发展了超低数据量(48字节)人脸识别技术及浮动网格的人脸与表情自动生成等实用技术。
在科研工作上,他一心求“新”。关于此,王守觉有一套“花匠论”。
“从邻居园子里摘一些花插在花瓶里,既美化环境,也能使我们认识更多花种,这是很有必要的;但它不能代替翻耕自己的土地并播下自己的花种。”王守觉说,“我们要从邻居那里取得经验,根据自己土地的情况耕作,长出自己的花,哪怕相对较小和较少一些……我们不做美丽鲜花的观赏家和评论家,愿做平凡而艰苦劳动的花匠,在生产实践中去找我的耕作园地。”
1984年,王守觉被派往美国几所大学作学术交流报告,落实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杰出学者互访计划。几次会后,不断有中国人问他:“你在美国待了多少年?在哪所学校念的书?”
这让他哭笑不得。他感慨:“百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现实,使中国民间和社会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洋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这就对中国超越‘洋拐棍’的工作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我第二阶段这30年来的工作说明了中国人是聪明能干的,任何新领域只要按照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明的规律性,破除对洋人权威的迷信,刻苦拼搏,就能在5年左右时间走到学科的最前沿,接近或超过国际上的最高水平。”
王守觉曾对参与撰写他科研活动传记的作者团队说:“我的科研活动传记第一阶段工作很好写、很明确,但第二阶段工作很难写,因为不少工作都是‘开着口’的,有待进一步系统化与完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希望我第二阶段的科研工作能够成为年轻人超越世界最高峰的一段梯子,在科学方面实现中国梦,也实现我的梦。”
(《中国科学报》)

 晋公网安备
14010702070607号
晋公网安备
14010702070607号